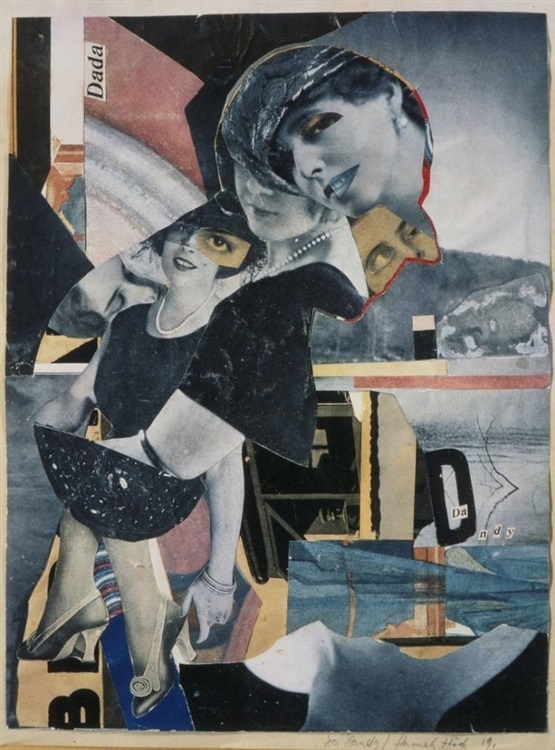现在,我也突发奇想,给这个章节写上了一份结语。
也许我可以自称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读者,但我在决定成为作者(非职业)的写作之路上也仅仅是走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而已。
我记得,最初我是在2016的冬天阅读完有关尼尔·唐纳德·沃尔什的几本知名著作的,可以说我的思想启蒙也是来源于1995年新时代运动浪潮后的余波。
在阅读完尼尔·唐纳德·沃尔的作品后,我便痴迷文学和哲学书籍,与此同时,我对于通俗小说和叙事电影热爱的情绪高涨到堪比我对星球大战、DC、漫威等大众漫画的热情。
灵感这种东西很是奇妙,都说生活需要艺术填充,而艺术来源于生活,在目睹探讨人性与神的对话后,我结合自己的喜好,便就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应该创造一本属于我的书。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之路。
我的创作灵感大多数都来源于诗歌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诗歌以波德莱尔和哥德的作品居多。(《恶之花》、《浮士德》是我的最爱,在这本书里你也能看到它们的影子)而《核冬元年》的前四章,是我在17年多个草案中写的一本独立的科幻短篇小说。
而从第五章到第六章的原型,则是我草案中的另外一本名为《出头鸟》的科幻短篇小说。
回忆起我能鬼使神差将两者融合成一个全新的故事的原因,我也只能说是直觉和灵感作祟。但正是这种变换促使了《核冬元年》有了更多推进的动力,使得我能继续向下写。
于是我开始创造莫哲的故事,医生的故事,安德森的故事以及更多人的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我将这本书的地位拉到了一个我心目中较高的位置,且并不打算在短时间内写完它(现在依然有这种想法)。
当一本科幻小说在写作时转变成一本本质是社会小说时,它的科幻外壳反而让整本书带上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拉美文学的意识流风格也让叙事在外人看起来更加模糊难懂了。
因此,第二部分的创作相比第一部分更具有挑战性,我觉得它必须要更有文学感。
作为一位业余写作人士,很显然我缺乏专业人士的职业素养,时间一长,我的写作目的便一直在“兴趣”和“成就感”之间徘徊,也不知如何是好,如同波拉尼奥笔下的画家埃德温•约翰一样,作为颓废派画家的他,艺术追求的灵感来源竟然是自身对非艺术的、功利性的欲望。
都说经验主义领导了现代大多数人的认知方式。我仔细一想,也许我不妨来假设一下它的结局会如何。
终于,我在一个夜晚,明确了它的本质:
《核冬元年》必须是一本自我价值观的遗作。它是我内心设想中悲观主义的无底洞,也是我对虚无主义认知的最巅峰。
因为我意识到,事物的发展是有惯性的,我需要做的,只是将它写下来而已。
现在再回头看,《核冬元年》的第二部分更像是在强调关于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
对于名为“革命”的章节,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带着了一种会“颠覆一切”、“人民必胜”的思想。但也许事实也并非如此,正如大卫•芬埃德所说,“你需要知道面具之下的人是谁。”然后再去思考,自由和集体究竟会将人们带向何方。
202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