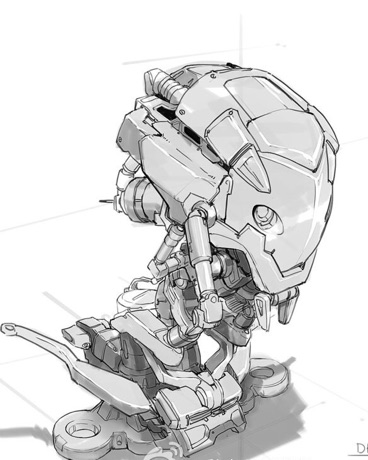-
 - 火种
- 火种
2017-01-07 08:03(7条回复)我不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你画下一只乌鸦,嘴里叼着什么东西;为了解释那块腐肉你又画下一只断臂——为了解释那残缺的中指,你只能再画下一地血迹。为了解释它为何如此不自然地立着,你又画下恰好卡着它的树枝,画下细长的棕黄色末端的一点嫩绿。当你沿着这条路追索下去:当你画下全部的树叶与树干,当所有色彩交织之时,你已经画下了那棵树,那棵与你开始作画时心里所想的腥红、残酷,和战争的焦土,和那乌鸦夜一样的羽毛都相去甚远的树。这就是你真正想画的东西。约瑟夫·布洛茨基言及此事,说:“诗学语言拥有——如同一般语言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特殊动力,并赋予心灵运动一种加速度,把诗人带往比他开始写诗时所想象得还要远的多的地方。”而到了我这里,我则要说,小说创作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解释和自我追索的过程,而探索最终的答案则是优秀作家应尽的职责。
最开始写下这段话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这段话太具有泛指的意味,而且特征也不明显。最终我还是打算把它写成书评,献给胃疼依然努力更文的铅笔。真有趣我的行为,就好像我正像第一段说的那样是个面对白纸的画家,将信将疑地画下了第一笔。
我相信铅笔在开始这篇小说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篇女主一开始就以傲娇的姿态出现的卖萌的小说竟然慢慢有了头尾,有了指涉,有了她想到和没想到的一切。仅仅刚到主线就过了七百收的成绩,我猜也是她当时不敢想象的。最开始时科幻与未来的外衣,似乎慢慢变成了内在的一步一步的追问与回答,铅笔对自己的要求也在随之提升(删掉了某些在内涵上过于彻底和露骨的章节,对话的描写也越来越凝练)。除了很萌的人物,你在阅读时似乎得到了什么别的东西,是你不加留意过的,或是平时不会去想的,你抱着放松的心态点进的这本小说竟然会再让你稍作停留,为了那个被殴打的机器人,想想灰色天空下人们的大叫和允许孩子们哭喊的地方的孩子的哭喊。或者是随手点进的这本小说居然会让你反复浏览,想想简单的对话体之间忽略掉的其他的心情、幸福、挽歌。又或者,不存在的“兰玲小姐”和“D-73”的投影中漏下的光线让你去想象了他们背后存在的或傲娇或任性的姑娘们,还有笨拙地爱着她们的小伙子们。时间不需要很长,哪怕有一秒也够了。我要说,铅笔是成功的。在这棵树上,在枝条的交错间藏了太多不属于这棵树的东西,一个娃娃,一把阳伞。到最终我们才看见画的本身并不是树,而是大野中央,树下的少女眼中暗含悔意。色彩改变了观者,亦改变了作者,色彩不需要很多,有就够了。是铅笔把小说带向了另一面?还是小说把铅笔带向了另一面?两种说法也许都是正确的,彼此包含,不能分离也不能对看。
城市的外面也许是丛莽、山岭或是另一座城市。活在城里的人无论是克制住不去想象还是根本无力想象,在红日升起之时也无法不去想到那金色同样遍布到的地方,而如果光芒不来自于太阳,也会使他们向深邃的黑暗的街道投去哪怕一眼的目光。成为一个这样的小说作者是快乐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她把你带到了别处。不管我开始时指望了些什么,改变意味着一切都在滑行。一切都尚未决定。更令人欣喜的是它在往好的方面生长,铅笔的小说无愧于我所说的,努力在为她的问题塑出形状,而问题也为她的努力而塑出形状。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写这篇书评呢?我知道写得很莫名,第四段的逻辑简直乱死。暂且不管这些,我想回答第二段的答案是,其实生活也是一个作画的过程,只是,能让我们决定的地方太少。因此小说的意义才弥足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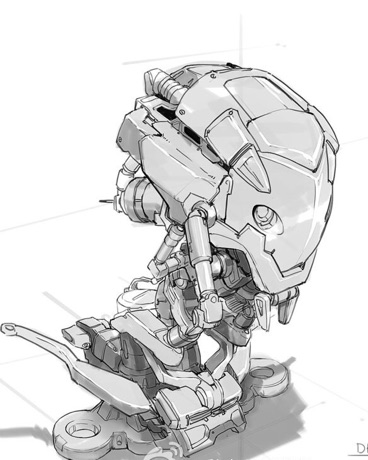
- 《人类,真是不可思议》9.8
治愈 /
- 7
-
 呓语7659 灰烬
呓语7659 灰烬
17-01-07 10:56回复朋友,你这书评是个技术活,可惜没法赏。
-
 雪韵千秋1315 灰烬
雪韵千秋1315 灰烬
17-01-08 05:20回复[em:sfgirl:019][em:sfgirl:019][em:sfgirl:019][em:sfgirl:019][em:sfgirl:019]
-
 Assamite 星星之火
Assamite 星星之火
17-01-08 09:25回复可以可以,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书评。小说深刻起来连书评都文艺。
-
 妄想罪孽。 灰烬
妄想罪孽。 灰烬
17-01-08 13:04回复你很6哦,朋友
-
 奈与白灵 灰烬
奈与白灵 灰烬
17-01-09 00:38回复强强强。。
-
 永夜_悠 火种
永夜_悠 火种
17-01-09 15:53回复很棒!